辩题 科学伦理是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 (2019-12-11 第8版 校园)
从科学角度而言,科学研究的范围是否有边界?纵观人类历史,突破想象的科学研究不少,但是突破伦理界限的实验等都不为世人所接受。科学伦理学的诞生无疑从某种程度规范了科学的发展边界。
就某种意义上说,伦理的约束对于科学的发展有时是正确的引导,有时却是“前进”的阻滞。面对一些科学研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是应该尊重人类社会的伦理准则,还是甘冒难以预想的风险而执着于人类前沿技术的探索呢?
11月13日辩论专版中刊登的“大学毕业生是否应该留在大城市”的辩题投票中,正方重庆大学支持率为32%,反方华东理工大学支持率为68%。
正方
温州大学
综述
开宗明义,科学伦理,是指人类伦理学为科技创新和科研活动提供的思想与行为准则;科学,是指人类拓宽认知、探索世界的实践活动,科学发展即意味着科学水平的演进。由于科学的发展事关人类文明福祉,出于对科研风险与收益的考量,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让科学健康合理地发展。而科学伦理就是长期以来对科技发展方向产生影响的“指向标”。讨论科学伦理是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实质是在探讨这一限制是否合理的问题,并对科学发展的限制条件进行反思与改进。基于此,我方论证如下。
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着眼当下,都不难发现,科学伦理与人们对科学发展的期待存在长期的不适配,相对滞后的科学伦理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古代,当人们还无法以科学手段解释一些事实或现象时,往往诉诸伦理,并以道德和教义迷信稳定人心;由此产生的科学伦理压制了当时的科学发展,使得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步履缓慢。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医生解剖人体并提出肺循环理论,但由于解剖人体为当时伦理所不容,医生被教会施以火刑,他的理论也被否定。这不是孤例,前前后后诸多研究解剖学之人都惨遭迫害,导致人体解剖学受科学伦理所限发展十分缓慢,以致许多本来可以被科学拯救生命的人选择了今天看起来荒谬至极的“放血疗法”;而中国古代对人体解剖的态度,相较西方更为顾忌。古语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使得人体解剖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的禁忌;再如禁止堕胎、禁止输血治疗等伦理约束,都禁锢着人们的科学探究。
当时的人们倾向于相信伦理、道德,相信神学、玄学,而不愿意相信人体学、神经学,并以滞后的伦理为据谴责和否定科学,以致阻碍了科学发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在,科学伦理对科学的影响仍然紧握住科学发展的咽喉。例如人类害怕生命科学的新尝试会危及生命伦理、造成社会紊乱,反对将胚胎干细胞和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但事实上这两种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运用实际风险性可以控制得极小且收益很大。其将实现HIV、癌症晚期等许多重症病的临床治愈。
因此,一味依照这些不适时的生命伦理限制科学技术的医学应用,无异于扼杀了现阶段人类与许多重大疾病抗争的可能性。在阻碍科学发展的同时,也让无数本可以被挽救的生命归于死亡,而这些结果仅仅是因为人类用伦理将可发展的技术束之于恐惧的高阁。
所以,我们应当对科学伦理这一限制进行反思,用理性照亮伦理保守的愚昧。归根结底,科学伦理是基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对稳定的追求而提出的价值导向。人们之所以反对克隆技术,是因为无法承受单一细胞的克隆能在顷刻间克隆出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自己的后果。基因编辑技术受到学术界抨击,不过是因为担心基因库的修改和对于想象世界中未知的恐惧;可是,当基因科学家一遍又一遍指出基因编辑的风险小而可控,给病人适用基因编辑技术,带去的是风险置换的机会,留存活下去的可能时,人类的伦理仍固步自封,不愿意迈出步伐。
伦理由人创造,人类认知的滞后必然导致伦理的滞后。害怕失序的保守确实无错,但我们希望的是能拯救人们的理性光辉。要让理性照亮伦理保守的愚昧,让科学发展泽被更多人。
答反方问
1.许多技术的发展并未成熟,人类限制技术的使用恰恰是为了避免这项技术应用在人身上会产生恶劣结果,当时关于输血的伦理观念保证了在输血技术不成熟时不会有人因为盲目输血枉死。今天学界对于基因编辑等技术引用在医学领域仍然存在争议。贺建奎对双胞胎婴儿进行基因改造,试图防范艾滋病。《自然—医学》期刊发表的最新研究表明,经贺建奎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孩,可能发生基因变异,令其寿命缩短。因此,科学伦理恰恰能防止不成熟的技术应用危害人类身体,您方怎么能给它扣上一个阻碍科学发展的帽子呢?
叶东朔:并非是扣帽子,其间的误解需要阐明。可能是由于对方辩友对基因编辑技术很多的运用没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对于我方所说的“让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临床医学阶段”可能出现的后果也没有进一步的思考。贺建奎之所以被谴责,源于他没有经过伦理委员会正当审批,以及在现阶段基因编辑技术仍然不成熟情况下的造人尝试。
我方对于这样的现象同样表示反对和斥责。可是,临床医学试验的治病救人和贺建奎因为一己私欲的造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临床医学讲究的是风险置换,特别是对于那些死亡率高达80%~90%重症患者,面对那些让人类长久无能为力的疾病(HIV等),从临床开始,一步步的尝试,才是我方今天提倡和站住的立场。
2.您方所举的无论是中世纪欧洲的例子,还是古代中国的例子,在当时科学还不是解释世界的权威,人们只是用玄学、神学解释世界。所以在您方论证框架中,无非是基于在古代,科学与伦理争夺解释世界的权力,所以您方所谓的阻碍只是权力争夺产生的弊害罢了,而不属于伦理。在当下,科学已经是解释世界的权威,如果仍违背科学伦理,它所产生的弊害是不是才反而阻碍科学的发展?
雷澳咪:神学和玄学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伦理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科学伦理从来不曾脱离人类伦理的范畴,无论是如您方所说对于生命的尊重,抑或是对于“人”这种特殊主体的尊重,都一直存在。
也正是因为这样,导致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试验等迟迟提不上日程;这也导致了明明有技术拯救这些病患、给予他们生机的我们,只能冷眼旁观,让这个技术置于人类恐惧的高阁上。
3.我方态度是一项科研即使利益再大、风险再小,也不应该要求人去承担其中那部分不可控的弊害,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科学实验用小白鼠而不是人类活体。所以其实本质上是双方态度的不同,您方是认为为了也许能达到的科学成果,可以让被基因编辑儿童承担寿命减损的风险,可以让克隆人承担丧失人格权的风险吗?
孙玲莉:您方其实对我方的诉求了解得并不够深入,我方并没有说是需要跨越式的直接研究基因对于人体改造,直接免疫HIV。我方希望的是放开基因编辑技术在医学上对于重症临床试验、治病救人的限制,让基因编辑技术通过实证获得进一步发展。
您方的质疑,我方明白,可是我们对风险的很多幻想都是基于对技术的不了解,以及对医疗底层逻辑的不了解。医疗上的风险置换指的是,对于这些死亡率高达80%以上的重症患者来说,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存在缺陷,只能给予他们40%的希望;但这相比于原先几乎是和死神打招呼的未来,是不是多了许多的可能?
因为各类重病,每年离世的人、每年破碎的家庭,对他们,合理地放开,带来的是面对死亡不再惶恐,面对明天更有希望。
结论
对于本辩题,我们双方在一起探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前提上的分歧,针对分歧做如下总结:
第一,双方对于科学伦理的定义不同。对方辩友认为科学伦理天然就是伦理中所有有益部分的结合。可是“伦理”这个词本身指代的模糊性,就让科学伦理在具体运用中和伦理从来是分不开界限的。如果为了辩论专门营造出科学伦理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伦理两词之间的区隔,以达成论证,未免有不贴近现实情况之虞,这样讨论容易让辩论流于理论。
第二,科学伦理发挥了作用并不代表没有阻碍。其实阻碍和助益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我方当然不苛求您方要论证到没有任何阻碍。但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在医学领域对于死亡率极高重症患者的运用和将胚胎干细胞作为科学实验对象这两个例子的探讨,都是基于有比较大的现实需要和并无太大风险之下的尝试,可它们为伦理所不容,因此无法展开,使得其实在上世纪就获得突破的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毫无用武之地,也无法发展。这样的限制究竟好不好,可能才是进一步探讨的核心。
最后,我们双方最根本的分歧是对科学发展态度不同。您方期待的是到万事俱备再开始,而我方认为需要亦步亦趋地尝试发展。确实前路可能迷茫、可能混沌,可能不知所终,但是积极地探索求新,在稳定范围内不断突破,这才是科学人应该有的态度和前进方向。
(综述由雷澳咪、孙玲莉撰写,结论由叶东朔撰写)
反方
华侨大学
综述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让人类见证了科学造福世界的无穷潜力。但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极强的自主性,在经历一系列惨痛的教训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不能毫无约束地发展科学,于是,科学伦理应运而生。
科学伦理是指人们在从事科学伦理实践活动和科研成果应用过程中对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和社会公众使用技术产品中所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这种观念和规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限制存在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不是阻碍科学发展的表现。恰恰相反,科学伦理维护着科学与人之间关系的两条底线。
第一,科学的内在核心价值不是无止境地追寻真相,而是要为人服务,这首先决定了它不能影响侵害到人的权益,不能对人的身体、心理、自我认识等方面造成损害。而且,作为帮助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我们必须要保证科学的可控性,才能更好地让科学造福人类。一旦科学脱离了人的掌控、朝着危害人的方向发展时,我们无法估计科学的无穷力量,假使不从一开始就禁止,有可能会造成覆水难收的恶劣局面。第二,不得以侵害少数人的权益造福大多数人为借口进行科学研究。
回顾那些不被伦理接受的实验或产品应用,无不是突破了以上两条底线。小到瘦肉精的使用危害人的身体,大到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以研究病毒解决难题为名残害犹太人。这些科学实验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也就是人的利益,违背了科学发展为人服务的目的。因此科学伦理对于这些实验或产品的约束不是在阻碍科学发展,恰恰是在维护科学的初衷,保障科学效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提倡科学伦理的应用还能够促进科学研究向着“善”的方向不断发展。
美国哲学家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指出,任何人做出选择时会受到自己内心价值判断的影响,内心的观念会外化成行为规则,成为行为习惯。科学伦理的诞生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科学为人服务的核心价值。只有我们不断地强调、完善科学伦理,才能使得有限理性的科学研究者牢记科学的边界,追求真理的同时保证研究行为会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科学伦理不会阻碍科学研究的发展,还能引导科学研究向好的方向不断进步。
答正方问
1.当下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在临床上治疗数百万地中海贫血症、镰刀型细胞贫血症、HIV、肺癌晚期等病患,且几乎没有污染人类基因库的危险,也符合医疗治病的风险置换逻辑。该项技术并未违反您方所提出的两条底线,但却为科学伦理所不容,迟迟不允许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阻碍其发挥治病救人之功效。这难道不是滞后而保守的生命伦理在阻碍科学之发展吗?
吴洁如:首先,就目前而言,基因编辑技术尚未成熟,仍存在许多争议,投入到医疗领域中带来的未必是人类的福音。病人无法确定自己进行实验后要承担的风险是什么,这与医疗中愿意承担已知风险换取疾病治疗的可能性不同,并不符合所谓风险置换的原则。而且,这些技术的不成熟并不能够在医疗领域造福人类,相反可能会造成危害。
第二,除了讨论在医学治疗方面的作用外,类似这样的技术更多在是否侵害了人权等方面存在争议。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如若不加以限制地发展和运用,意味着未来我们可以订制人类,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样的全由他人决定,人类将在他人的生命中扮演上帝的角色。同时,还会造成克隆人等技术导致人权通货膨胀和给人类带来情感冲击等一系列问题。科学伦理约束这些实验才是在保障人类社会的稳定运行。
2.科学发展的确不是越快越好,但是伦理的限制好像并不如对方所说仅是将科学置于可控范围内。基于此,希望对方辩友进一步解释为何您方只看到一部分伦理将科学发展限制在合理的范畴内,而历史上伦理对科学发展的压制又为什么不是对科学发展的阻碍呢?
李沂晨:我们所认为的科学伦理首先肯定了科学的积极作用,只是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规范和限制作用。然而在对方辩友所提到的历史中,封建神学、玄学占领着统治性地位,科学并不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换言之,您方举的例子中的伦理本已与科学站在了对立面,注定会阻碍科学的发展,也并非我们今天所真正想讨论的科学伦理。
其次,您方至少也承认了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伦理对于科学的规范起到一定的有利引导,只是在质疑一部分科学技术因为人类道德伦理上的不认同而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您方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类似基因编辑技术的危险性我们都有目共睹,经基因编辑后的人类是否会更长寿、人类基因库是否会遭受污染完全就是未知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科学抱以敬畏之心,以谨慎的态度行事未尝不是件好事。
3.由于人类伦理发展和演变较为缓慢,往往和当时的科学发展不能适配;古往今来,诸多科学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伦理阻碍。在对方辩友看来,这些阻碍是使得科学得以正确发展的原因。可事实上,中世纪的迷信、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解剖学的不信任以及后来对于开颅手术的恐惧,对于脑科学和神经学的畏惧,乃至现今,明明有了可以在医学临床治疗上与病魔斗争的基因编辑技术和为人提供健康器官的干细胞研究,人类依然将它们视作禁区,这期间丧失的千千万万患者的性命,是否是科学伦理的错误,阻碍科技发展的最好佐证?
李沂晨:您方所提到的中世纪的迷信对科学的阻碍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本就对科学抱持怀疑的态度,而封建神学则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伦理与科学的矛盾,实际上是神学、玄学与科学的对立造成的,如此得出的结论不够公允。而后来人们对解剖学、开颅手术等新科技的谨慎,只能说明新科学代表着更多的未知和巨大的风险,当一项技术在尚未成熟、其效益也未知时,我们有理由和责任仔细掂量其中利害。等待和适应并非是停滞不前,只是为了令其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所用。
此外,对方辩友认为现代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效益大而风险小”的观点也过于片面。首先,这类新技术的正面作用往往被资本过分放大,使得人们只关注到其有效性而忽略了隐含的巨大风险。这种时候,保持理性,以科学伦理所宣扬的观点辩证看待、谨慎处之反而更为安全可靠。其次,再拿基因编辑技术为例,如若该技术得到广泛推广,这势必会造成永久性的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有钱、有权的人会率先采用此类技术修改自己后代的基因。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双向流动将会在社会上永久消失,进而导致人类社会的彻底分化。而这恐怕是对方辩友未曾设想过,我们每个人也都不愿看到的。
结论
总结一下,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才是违背科学伦理,一个是我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科学发展。
首先,科学伦理的设定本身就是用来规避无法预见的弊害,这点双方达成共识。您方认为贺建奎之流与基因编辑技术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完全违背伦理,一个是有可控的风险,所以两者本质上的差别还是风险差别,在您方框架下,如果贺建奎的研究达到了所谓“风险置换”的标准其实也是可以进行的。即使您方“风险置换”成立,但为什么当下仍不进行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不正是因为这项技术的风险还没能达到可以置换的条件吗?所以当下科学伦理的违背与否,是风险能否被承担的差别,只不过曾经的风险是信仰破灭、教条紊乱,当下则是试验失败的弊害。观感不同,但机理相通。
其次,我方也承认科学进步必定承担风险,也不要求一个万全之策来辅佐科学进步。我方想说的是科学伦理能够规避那些不可控的风险,我们只有尽量远离它们,才不至于使科学的方向与为人服务的目的相背离。即使这样的风险已经低到了您方所认为的,可以进行“风险置换”的情形,我方也认为不要要求那个99%会死亡的病人配合研究。因为人从来都不应该是科学发展的试验品,他在生命消逝的最后一瞬都应该保有其人格权。而那些为了科学、为了某处那个5岁的地中海贫血症的小孩能活下去,而自愿让渡自己的权益支持科学研究的人,我们会称其为英雄。科学伦理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赋予了这部分牺牲者更为伟大的意义。
(综述由吴洁如撰写,结论由梁瑞宇撰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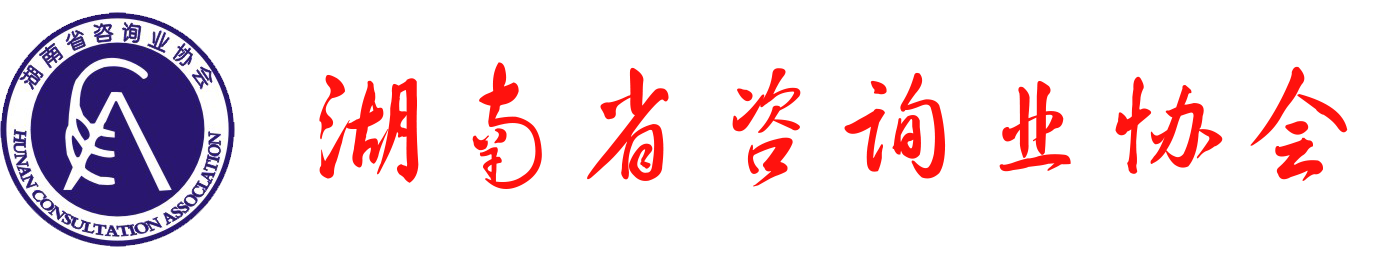
 点击打印此页
点击打印此页